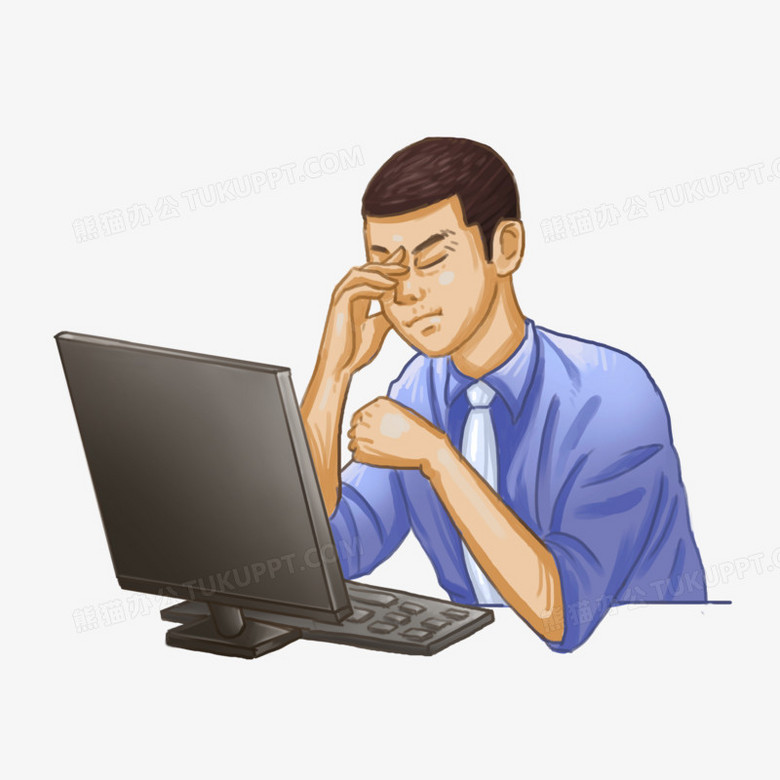前两天是辩论赛的明星周。太多好的题目被搬上来,诸如”生与死“,”意义的建构与解构“,”人生的轨道和旷野“,”缺爱与否和爱的关系“,”祛魅 / 赋魅和幸福的关系“。
真理是不是越辩越明我不知道,透过辩论想看到的是不同立场,思维,意识形态的碰撞。
但是不可避免的是,竞技辩论是需要争胜的,奇葩说是需要煽情的,主办方是需要流量的。这种情况下,恐怕某种程度上形式已经重于内容。
所以对哲理辩,大师赛有更高的期待,哪怕是在这样的现状下,也有更多的深刻的空间,在交锋之余,对灵魂发出的拷问才是辩论赛真正的意义。
记录一下哲理辩和大师赛决赛的主观感受
缺爱/不缺爱的人更懂得爱人
必须讨论的问题是,缺爱和不缺爱之间的这条线怎么画的。以及更懂得爱人和缺不缺爱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什么?
有答案,缺不缺是一种主观感受非客观状态,时而缺时而不缺。联系是模仿,是基于反馈的强化学习。
讨论到这里,恐怕不得不问出一个问题,爱人的能力这个东西到底是天生的,自发的,刻在基因里的还是后天学习到的?如果是自发的,天生的,每个人天然有爱人的能力,和缺不缺没关系,比不出来。如果是后天学习到的,那就简单的不缺更懂,同时导致傲慢,没人比我更懂爱。
用因缺有需的逻辑只能论证我缺少被爱,需要被爱,然后越缺,越需,越求,越怕失去,越失去。
抛出了几个论断。人终将缺爱(孤独)。不缺和傲慢,缺和自卑。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反馈系统,人生来就在强化学习。
引出的思考是:爱从何处来(自发or学习)?爱往何处去(存在焦虑下,怎么看待爱与被爱)?
当今时代,我们更需要意义的解构 / 建构
哲理辩可称得上华语辩坛最高的舞台了,而漫士沉思录给的这个题目也的确配得上这样的场合。
解构和建构本身是一种纠缠态,在这样的场景下论证当今时代更需要,必要。
自己的看法,不断解构到最后就剩下虚无,泛娱乐化,无意义,建构就是在赋予意义,但建构到最后就是规训,就是话语体系,就是权力。
酒神和日神的对决,流动的意义和理性、秩序的碰撞。
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之下,建构是必不可缺,上海豪车游街,正是那句很有争议的”他们穷的只剩下钱“,而陷入自我狂欢的老奴,除了建构,别无他路。建构理想,建构爱,在虚无的世界中寻找一点真的意义。对自己来讲,同样的,解构到最后,追问到最本质的问题,理想不过是依赖于社会文化背景、语言系统、个体心理等多种因素的交织与互动,爱是文化、社会、历史的塑造,权力、主体与客体的互动,以及情感与理性的交织,然后呢?解构到一切没有意义之后,看到了所谓或真或假的本质之后,然后呢?恐怕还是需要建构新的东西,这也是解构之后的建构,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。
面对这样复杂的现实,怎么办呢?是握紧锄头?还是捡起金钗?还是高唱国歌?
抛出问题,这是辩论的意义,胜负不代表答案,没有答案,因为答案是自己的,不是别人给你的。尤其对于这种值得深思的问题,关注点是不同立场下的不同观点的逻辑链,也许每个视角都有圆融之处吧,每种立场都有合理之处吧。写到这里,还是要引熊浩在”宿命论可不可悲“中的一大段陈词。
他知道什么是对的,什么是错的,辩论就是要磨掉这种生命高度,让你在每一个立场的旋转当中去找,也许所有的立场当中都有可取之处,所有的观点当中都有为难之处,所有的立场当中尽是黑芒,也会有微弱灯光。你找到了,由衷感到高兴,就会觉得没有原来那么偏执。
他让你放弃那种居高临下的俯视,而让你跟众生、跟众念、跟凡俗紧紧的在一起,为所有不可理喻的事情去做辩护,为所有需要辩护的东西去伸张价值,这是辩手的基本素养。在某种意义上,辩论就是要你打掉可悲,从而涵养慈悲。阿伦特有一个经典的说法,他说当有辩论的地方,权威就暂时终止。什么意思?他说有辩论,你就在讲话,我就在聆听,反过来亦是如是,我就在讲话,你就在聆听,我们真正在交流。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,我给你辩什么?我命令你、教育你、指导你,我自上而下的以师长自居,你去实行就好,你去理解就好,你去学习就好,争辩个毛线。
正是因为我相信你也可能有可取之处,你也可能有合理之处,我们才真正让生命在这个意义上发生观点的交织,我们真正平等,你在辩论中剥去那些外部的枷锁,重新还原成真正的人。我重复汉娜阿伦特的这句话,汉娜阿伦特说:有辩论的地方,权威就暂时终止。我想做的是为辩论人做一个力不胜任的辩解。我们不是八面玲珑,我们是相信每一面都有可能有玲珑之处,我们是那群找玲珑之处的人,而这种观念不是可悲,而是慈悲。
猜你喜欢
发表评论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
评论信息
![]() 粉丝二号2025-01-22 20:43
粉丝二号2025-01-22 20:43
我知道有一句特别通俗的话,说难得糊涂一点~聪明的人会比较痛苦,但世界和生活的可爱之处就是在不断祛魅的过程中,捉住一点点确幸。